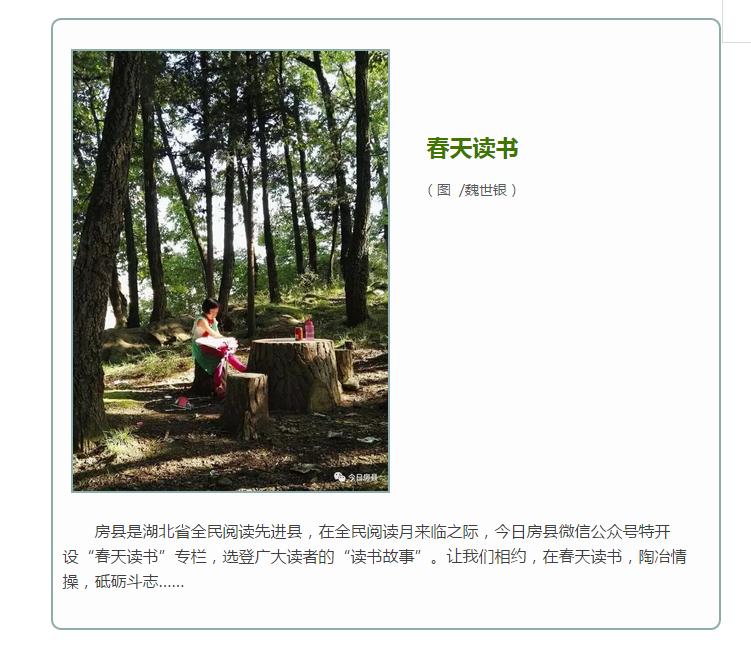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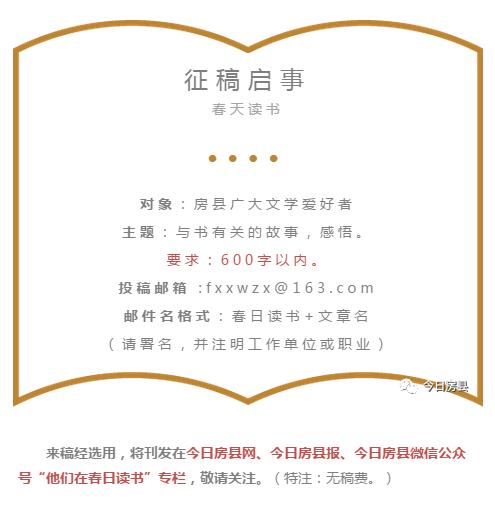

我的读书
□ 霍中南
说也奇怪,我们这代人走了几乎相同的读书路线图。
很小时,别人借本《西游记》,规定时间要还。除了上学,就拼命读。太阳落山,没有放下书的意思。有电灯,只有15瓦。母亲收去书,藏得再紧都能给找回来。眼睛从那时起就近视了。
文革了,没书看,实在无聊,断断续续听长篇小说连播《万山红遍》、《李自成》、《金光大道》等,算是历练我对文学的情趣,也是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最早的体味。后来又藏着掖着地读了巴金的《雾》《雨》《电》,囫囵吞枣地读了《红楼梦》以及《三家巷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。读书对心灵震撼大的当属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和卢新华的《伤痕》,有了太多的共鸣。张贤亮的《男人一半是女人》读得最细致,还在一个读书会上谈了体会,中国人最忌惮的“性”得到充分展示,似乎整个社会都是蒙住双眼,又从指缝中看。
在我教书和当创作辅导员后,读书杂。莫言、苏童、余华、王蒙、王朔、方方、池莉以及鲁迅、林语堂等,都能从中找到认同点。再后来搞戏剧创作,又读曹禺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原野》。读书,我并不反对“临时抱佛脚”。谁都不可能先知先觉,哪有那么多储存知识等着你用?
历史在前进,一代又一代人地出现,总会有超越,包括超越我们这一代,很正常。文学是人性的东西,不管环境如何变化,人性始终如一。不读书,不可能有文明的滋润,人无法有厚度,无法有爱,无法进取。简而言之,没有阅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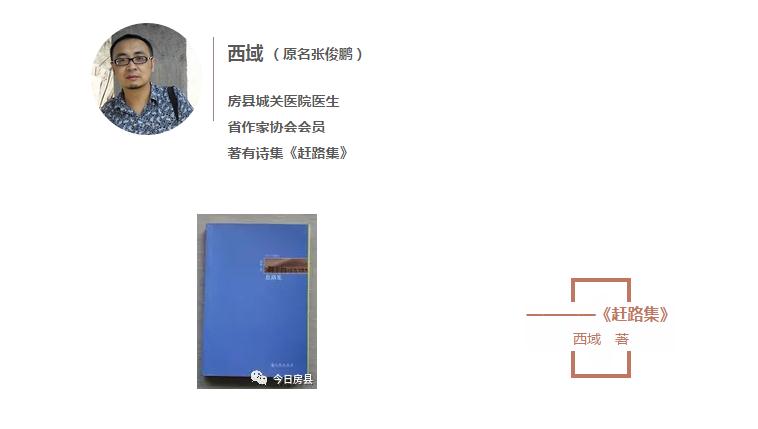
淘书记
□ 西 域
作家蒋子龙说:“书籍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大学。”这话给了没有上过大学的我以安慰,虽然我在这所大学里不断“旷课”、“逃学”。
2004年,蠢蠢欲动的我随生活之波逐流到广州中山四路。每天中午下班后,我溜达到邻近的广州图书馆看报纸杂志,顺便享受一下穷人们享受的免费空调。一次,图书馆关闭,我转悠到后门,发现地下室有一个“天天低价书店”,里面书价很低,还都是库存的新书,我像阿里巴巴发现了强盗的宝藏。
我在这儿买到的书有:民国上海著名医生陈存仁的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、《抗战时代生活史》、《我的医务生涯》;诗人北岛的随笔《青灯》、《失败之书》;以及《三国志》、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、《梦溪笔谈》、《随园诗话》、《容斋随笔》等。大部分书都便宜到让我像如获至宝的小偷一样惬意,又惊喜得直打哆嗦。其中,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三国志》、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都是轻型纸,厚厚的书拿在手里却轻如掌上小赵。尤其是十元买到了作家杨显惠的《告别夹边沟》,想到他写夹边沟多次深入实地寻找当事人采访的那个艰辛啊!就觉得很对不起杨老师。
在这个低价书店看书买书,让那个曾经漂泊的年代暂时栖下了无处置放的乡愁。在时代的喧嚣与嘈杂之中,人因为阅读变得耳聪目明,气定神闲,顿觉人事安稳,岁月静好。虽然,这样的日子像流烟与浮云,负驮着人生的伤怀悠悠远逸。
五年以后,我因事再赴广州。办完事后,从火车站转乘地铁、公交,像一个朝觐麦加的阿訇,又如一个赴花月之约的情男,一路直奔天天书店。当我兴冲冲地来到那个熟悉的地方,只见门庭依旧,春风桃花,却已是书去屋空。
那一刻,我站在原地好久,不想离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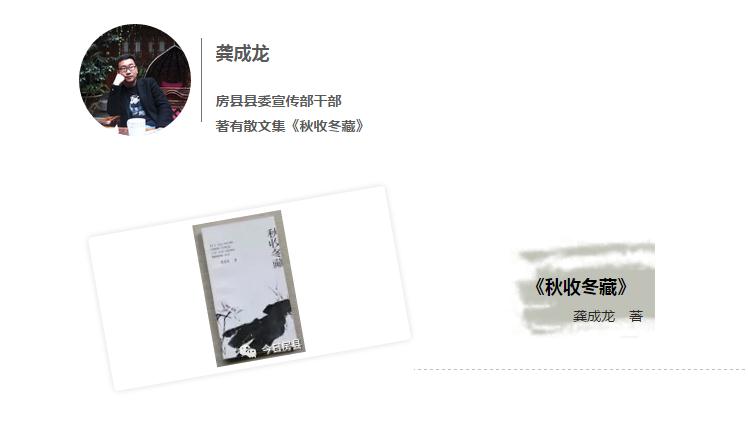
书 趣
□ 龚成龙
关于读书,有很多故事。比如,韦编三绝,高凤流麦,还有,程门立雪。
有很多书可以读。古人说,经史子集;我们说,人文,自然。因为个人偏好,更多的时候,我会去读,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明史》;或者,《湘西的“土家”与古代巴人》、《乡土中国》;又或者,《孙犁文集》、《北京法源寺》。
外公曾经自嘲,说自己是“闲人”读“闲书”。的确,读这些“闲书”换不来汉堡,换不来电影票,更换不来欧米茄……
七年前,我偶然间读到了刘九洲的《新闻理论基础》。我第一次知道,原来用哲学架构也能写出一本鞭辟入里的新闻学理论书籍。也是从那一刻开始,我决定报考华师新闻系的研究生。此后,我频繁往返于武汉和荆州。疲惫,却充实。后来,我成为一名记者,而读研,是在四年以后。
三年前,我和小师妹在苏州休假。行至枫桥,她开玩笑说:“张继也是,做官,就好好做官嘛。不写诗,也许官要做得大一些。可是,没有诗,枫桥怎么会美呢?雍正写得也好:‘维舫枫桥晚,悠悠见虎丘。塔标云影直,钟度雨声幽。’”后来,每每从湖北卫视看到她,我都会想起她在苏州的样子。那是我见过的,最美的姑娘。
一本书,就是理想;一首诗,就是爱情。读书,也许离“实用”很远,但是离人生很近。它会让人变得有趣,因有趣而有情,因有情而热爱生活,因热爱生活而坚韧。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完美,但从不苟且。












